22年前的一天,中国香港西南海域的海面上静静地停着一艘打捞船,在漆黑的夜幕下,它犹如幽灵一般。据一本收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馆里的古航海日志记载:1752年,一艘名为“歌德马尔森”号的中国商船,在这片水域触礁沉没。当年,这艘从广州出发的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准备驶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两百多年后,一个名叫迈克.哈彻的英国职业海上打捞者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自己的打捞船开到了这片海域。哈彻从“歌德马尔森”号打捞上来了青花瓷器23.9万件,每块重达45公斤的金锭125块。1986年,哈彻将这笔宝藏交给了荷兰嘉士德拍卖行,换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回报。从此,哈彻以“当代最成功的寻宝人”的头衔名噪天下,而“南海沉宝无数”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一批又一批的国际寻宝人来到这里,盗捞中国的水下宝藏。
南海沉宝堪称“海底瓷都”
其实,这并不是哈彻第一次从南海捞起宝藏。1983年,他就在这里发现了300多年前沉没的中国明代帆船,船内满载2万余件瓷器。这些瓷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以250万美元成交,平均每件价值112美元。第一次尝到甜头的哈彻,从此锁定了南海。他出高价雇来各种“人才”——考古专业的高材生、海难事故的研究者、东方海域的知情人,以及技术纯熟的潜水员。1999年,哈彻在南海又找到了一艘载有100多万件康熙年间四大官窑瓷器的清代沉船“泰星”号。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他竟然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拍卖。这一次他赚了3000万美元。
哈彻发现的宝物,或许只是埋葬在南海水下宝物的“冰山一角”。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贯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但是,在那个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时代,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随时会遇险沉没,几乎每隔29个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直到19世纪初,因遇上海盗和风暴而沉没的货船比例仍高达30%—40%。
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在中国的茫茫海域下“沉睡”着2000至3000艘古船,其中以宋元船居多。沉船中还有一些英国东印度公司和瑞典等的外国沉船。这些船满载的中国陶瓷、丝绸、金银珠宝等宝藏也就随船体下沉被大洋淹没。有专家曾表示,这些沉船完全构成了一个“海底瓷都”,其数量难以估量。对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中国的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宗教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将由此有新的延伸。可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标本,在海外盗捞者的眼中只等同于钞票。几乎就在考古学者深入海底的同时,逐利而来的各色人等也瞄准了发财机会。
海外盗捞者野心勃勃
在苏富比拍卖行,一件中国元代青花瓷罐曾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引诱着越来越多的“哈彻”加入到沉船打捞的队伍。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他们不惜血本,利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海域搜寻水下文物。与此同时,一些无力打捞本国领海内水下文物的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印尼、越南也开始与西方捞宝公司合作。他们向这些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在领海内捞宝,之后再与颁证国分享利润。不过,这些西方公司的勘查范围通常都不会局限在颁证国的领海内,而会秘密潜到中国海域盗捞水下文物。于是,南海成了他们满足欲望的“乐园”。盗捞、窃取、走私、拍卖……在中国海床上静躺了千百年的沉宝,也在通过一条条隐蔽的商业通道流失。
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费尔.格雷科就借与菲律宾政府的合作,盗捞了数万件中国古董。为了“开发”南海宝藏,格雷科在菲律宾至少住了10年,从当地渔民的讲述中一点一点搜集沉船信息。据菲媒体披露,从1997年到2002年,格雷科先后在南海发现了16艘沉船,捞起了约2.3万件古董。这些文物都悉数被他运回了美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和《纽约时报》的记者曾到过他位于洛杉矶的住所。据他们形容,格雷科的花园里赫然立着几个两人多高的巨型花瓶;一大堆精美的瓷碗、陶碟被随意摆在地上,“整个家就是小型中国古董博物馆!”发达的互联网让格雷科轻易绕过公开拍卖文物的法律障碍,将古董卖给了私人收藏家。这一点让菲政府异常恼火,曾发出逮捕令并要求美国将其引渡回菲律宾。但美国拒绝配合。
今年50岁的德国工程师蒂尔曼.沃特法有个野心,他要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网打尽”南海最重要的海底宝藏。1998年,他在印尼勿里洞岛(位于南海与爪哇海之间)附近水域20多米深的海底,找到了好几万件保存完好的陶瓷制品。沃特法将这座海底宝库取名为“黑石”号。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先后捞起6万件唐代文物,包括陶瓷酒壶、茶碗、刻有浮雕的金银餐具等。研究推测,“黑石”号很可能是在穿越爪哇岛途中,遇上暴风雨触礁沉没的。据中方考证,“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品种相当丰富,有很大一部分在中国都没有出现过,“黑石”号的青花瓷也是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对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非凡。然而,在中国几家博物馆与沃特法的接触中,沃特法都坚持把“黑石”号的绝大部分出水文物打包,以至少3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而这是中国的博物馆所无力承担的。从今年年初开始,沃特法竟将他的捞宝工具伸向了中国南海。据印尼海洋渔业部估计,在“印尼周边”的南海海域,有至少463艘货船残骸,许多船龄超过1000年。鉴于沃特法的“成绩”,印尼政府打算将这463处南海沉船位置,尽数交给沃特法的探宝公司。
金融投资家、比利时人吕克.海曼斯也是印尼政府的“合作伙伴”。2004年9月,海曼斯勘察出了一艘来自10世纪的中国沉船,船很大,有70米长、15米宽。他在船队上坐镇19个月,指挥潜水队下潜2万次,把将近25万件珍宝逐一打捞上来。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些瓷器:碟子上的饰纹是龙、鹦鹉和其他异鸟;茶壶上清晰可见莲花的图案;青瓷上的釉完好无缺。巴黎博物馆专家保罗.德斯卢克对海曼斯说:“知道你捞上了什么吗?公元10世纪的沉船极其罕见,我们对五代十国的认识非常苍白,博物馆里的文物极少,这艘船填补了空白。”在打捞这艘五代十国时期沉船时,海曼斯还在附近海域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不明物体”,但这处沉宝所处海域相当敏感,是印尼与中国有争议的水域。就在他打算对新宝藏“动手”时,印尼警察突然查封了他在雅加达的藏宝仓库,并指控他“非法捞宝”。海曼斯猜想,这也许是已经掌握了打捞沉宝技术的印尼政府想甩开他单干。
寻宝热将毁掉很多宝藏
除了国际盗捞者,国内也有许多文物贩子在盯着南海的宝藏。尽管我国早在1989年就对水下文物进行立法保护,但已发现的古船文物还是遭到当地一些渔民的哄抢。他们捕鱼时有时候会一网拖出瓷器或古钱,便知道下面有沉船与宝物,于是就借机打捞,而有组织、有规模地**这些水下文物更是防不胜防。中国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告诉本报记者,在国内,盗捞海底文物的“销售”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通畅的渠道和市场。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盗捞行为,都会在造成中国文物流失的同时,使这些文物的考古价值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的水下文物于1987年成立的。而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的即将出水,就是这个中心的杰作。张威说,目前制约我国水下考古的头等问题就是资金。国外的水下考古都有企业赞助,但中国目前只有香港一家企业曾出100万元赞助打捞“南海一号”。张威说,沿海调查一次就要花100多万元,到一趟西沙来回要300万元,一套潜水服要4000多元,就连一支深海灯也要1万元,水下考古无疑是个昂贵的行业。被称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甚至曾建议中国不要搞水下考古,因为太费钱了。
盗捞者为何肆无忌惮
至于外国打捞公司为何能频频潜入中国海域,进行商业性盗捞或在其他海域打捞中国沉船,专家分析,这是因为无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界定都太模糊。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林灿铃认为,目前我国相关文物法规定,“对于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对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样的法律界定都是不够准确和完善的。因为对于中国领海外的其他海域可以确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它仅仅是规定了辨认的权利,也就是说仅仅运用了文物的“属地原则”,而没有追究文物的“属物原则”,这显然不利于我国文物所有权的保护。而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就采用双重原则,有利于其追讨文物。此外,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两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内海洋文化遗产的归属,我国法律也没有做出任何的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目前国际通行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给商业盗捞留下了法律漏洞。该《公约》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内的海底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且特别强调对这类文物“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公约中提出的这些条文大多概念含混不清,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来源国难以依此追讨自己应有的权利。
名称:元青花鬼谷下山罐
制造年代:1351年左右
类别:青花瓷。青花,即元代的青花瓷器的简称,早已被中国陶瓷界认定为与唐三彩一样的专有名词、专有品牌。元青花的釉料,主要为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且大件精品主要供出口,供中亚、欧洲宫廷贵族赏玩、珍藏,故元青花留给后人的谜语最多。
最后露面: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
价值:2770多万美元(2005年)
流失时间: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一位驻北京的荷兰人购得。持有者:可能是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通过古董商埃斯凯纳齐在2005年7月伦敦佳士得拍卖会拍得。埃斯凯纳齐是国际知名的几大古董商之一,在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同时,也代表一些大买家购买顶级艺术品。委托他的既有西方金融大鳄,更有石油巨头。
流失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曲折经历:
元青花鬼谷下山瓷罐最初是20世纪初荷兰人范赫默特男爵在中国偶然购得。事情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在1913-1923年期间,赫默特男爵在荷兰海军服役,被派驻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负责德国及奥匈帝国等使节团及领地的安全。
赫默特爱好艺术,收藏广泛,对中国瓷器的喜爱可从他当年北京旧宅的相片上窥见一斑。他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最为精美的就是这只青花罐。有趣的是,他购买这个鬼谷下山罐时,还以为那是明代的青花罐,因为当时一般认为元代尚无能力制作出如此工艺精湛的瓷器。
蒙古统治时期,青花瓷件数少,易被人遗忘。西方收藏家一直到1968年克里夫兰美术馆举办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展览后,才开始青睐元代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元代青花渐渐受到重视,但没有发现多少堪称传世之作的元代青花。
赫默特的后代和他一样并不知道瓷罐如此之贵重,因而多年来并没有对它有什么特别关照。60年代时瓷罐曾被赫默特的第一代后人拿去估价,但专家也误以为是明代青花瓷,当时认为值2000美元。主人居然将价值连城的珍宝当草,把它当作盛放DVD光盘的坛子使用。2005年,佳士得专家再次拜访才发现“这件瓷器太棒了”,赶紧让主人把原本放于罐内的DVD光盘另觅他处存放。
事实上,直至佳士得出版了拍品目录,收藏者才得知瓷罐的存在,瓷罐也开始在国际收藏圈内引起极大关注。历来古董商非常看中物品来源。由于此罐来源明确,自1913年至今一直在一个家族收藏,并且以前未被世人所识,是行家眼中的“新鲜货”,所以一旦披露,市场兴趣很高,深受藏家重视。中国人的激情也被激发,因为其他七个同类古董无一留在中国。
2005年三月开始,佳士得把瓷罐相继在纽约、日本、香港、上海、北京、台湾、荷兰、法国等地巡回展览,使得人们对藏品的感性认识不断增加,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拍卖前,专家对瓷罐的估价为100万英镑,也有人说拍出500多万英镑没有问题。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中国部专家连怀恩的估计是600万-800万英镑之间。
回归难题
2005年佳士得伦敦拍卖会之前,有一些中国内地和台湾的藏家跃跃欲试,希望夺回国宝。内地藏家由于经济实力有限,有几位原打算集体购买,终因操作困难无奈放弃,而台湾几位藏家则是以协商的方式,把“夺宝权”“礼让”给了开设有“陈氏博物馆”的陈得福,由寒舍公司总经理王定乾代表陈先生出面竞标。王定乾颇有感慨地对媒体说:“有幸恭逢其盛,参与竞标。虽失之交臂,憾失国宝,但虽败犹荣?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中国文物创下世界(瓷器)最高价格,而更象征着中华文化的艺术价值与内涵,受到国际人士的尊崇与肯定。”
连怀恩强调,在拍卖中,竞拍者未卜先知的能力十分重要。最热门的东西常常会出人意料,通常竞买者会准备额外金钱作后盾。他认为,此次中国藏家没有竞得瓷罐并不意味着中国买家没有能力,而是拍卖前计算有误,因而真正面临意外高价时一时缺乏心理准备。事实上,中国藏家实力很强,如果计算好,完全有能力购买。中国人参加元青花罐竞拍虽多少有些让中国藏品回归故土的因素,但连怀恩认为,他们并不是要扳回所谓中国人的“面子”,而是因为此罐品质的确非常好。当然,让此罐回到亚洲,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学术研究的确有很大帮助。
同类国宝
品类纷繁的元代瓷器中,青花瓷器以鲜活、艳丽、明快独树一帜。青花瓷器中,以人物故事为装饰题材的最大特点。这些所绘的人物故事在明清以后不再多见,明清时期所绘人物大多为市井俗子、婴戏、吉祥人物、田园逸士、英杰明儒、神怪六类。也就是说,元代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具有特定历史内涵。青花瓷器的数量极少,绘画技法高超,特别是画面小中见大,且多表现元代杂剧的故事场景,开创了全新的视觉领域。
目前所见到的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瓷器不过几十件,而且相当一部分流失海外,国内所见者区区可数,主要有以下这些。现藏于江苏省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出土于江宁县牛首山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墓中。画面在梅瓶的腹部,占据主要位置。上下饰西蕃莲、杂宝、变形莲瓣纹、垂珠纹等。主题鲜明突出。画面中,主要人物萧何头戴展脚幞头,着袍束带,五络须髯。左手控缰,右手挥鞭,策马飞奔。画面的另一侧,韩信头裹软巾,身着长袍,手牵战马在溪边饮水。空白处衬以苍松、梅竹、山石,错落有致。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青花瓷罐,内容为《尉迟恭单骑救主》,画面一侧单雄信双手持矛,纵马前冲。另一侧有身着团花锦袍,骑在马上的秦王李世民和手持钢鞭的尉迟恭。两人并辔而行。李世民头微侧转,尉迟恭左手指点,两人似在交谈。尉迟恭身后,一卒双手擎旗。大旗上直书“唐太宗”三字。
“蒙恬将军”玉壶春梅瓶出土于湖南常德市,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画面中蒙恬顶盔贯甲,面相威严,端坐在椅上。其后一武士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大旗,旗上直行书“蒙恬将军”四大字。蒙恬的前方一名高鼻深目,手持弯弓的武士前来禀告。武士的身后一头戴毡笠,短衣束带的士卒右手按一抓来的官吏,此人戴高冠,着花袍,作汉人装束,跪伏于地。整个画面绘蒙恬将军审讯战俘的场景。蒙恬满面钢髯,端然稳坐的姿态,以及背后高高树起的大旗,展示了巍然肃杀之气。
湖北武汉市文物管理处收藏的一件瓷瓶,瓶腹绘出四个莲瓣纹菱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有王羲之爱兰、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林和靖爱梅鹤四个画面。画中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拽杖,或在柳阴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四个不同的画面表现了共同的高雅闲逸的主题。
流失在海外的,以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昭君出塞”图青花盖罐最为出色。这件盖罐罐腹绘九个人物,七匹乘骑(另外两骑当隐在山石后面)。九个人物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骑在马上,或摇鞭步行。马上驮着弓、行囊。观人物相貌、服饰有差别。其中骑在一匹白马之上,怀抱琵琶,梳高髻的汉装女子是王昭君,前后各有一胡服女子随行。六名男子中,有的头戴貂冠,髡发驾鹰,着胡服;有的戴毡笠,着汉装。当是迎亲的匈奴使节和汉朝送亲的官员。画面中山石掩映,苍松、翠柳、修竹、芭蕉杂衬其间。疏密有致,布局匀当。
1994年香港苏富比拍品中有一件“三顾茅庐”青花盖罐也很精致。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有一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戴交脚幞头,着长袍,躬身拜谒。关云长和张翼德在一边窃窃私语。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刻划得淋漓尽致。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同一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画面有所变化。诸葛孔明箕坐在茅庐之内,正在悠闲地观书,茅庐旁植松柏、篱笆,一名头梳双髻的童子打扫庭院。另一边是刘、关、张三兄弟。刘备居前,躬身施礼。
其他还有流于英国,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西厢记”青花梅瓶;1996年苏富比拍品“西厢记”青花盖罐;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吕洞宾”青花玉壶春瓶;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陶渊明访友”青花玉壶春瓶;1985年日本大阪《元代瓷器展》图册所录的“周亚夫军细柳”青花盖罐、“百花亭”青花盖罐等。上述各件无论哪件都称得上是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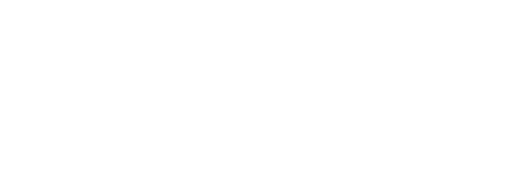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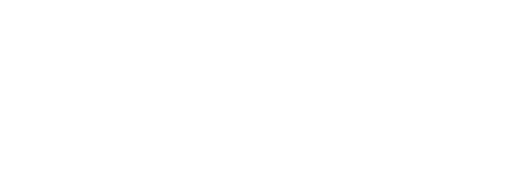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奥特号的签约作者“小萍”
本文概览:22年前的一天,中国香港西南海域的海面上静静地停着一艘打捞船,在漆黑的夜幕下,它犹如幽灵一般。据一本收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馆里的古航海日志记载:1752年,一艘名为“歌德马尔...
文章不错《中国的文物有哪些》内容很有帮助